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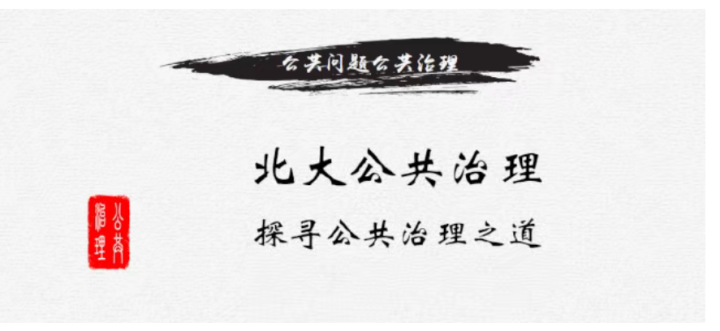 富邦优配
富邦优配
编者按
本文运用“需求-回应”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为应对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而发生的模式演进。研究发现,为回应不同时期的结构性需求,国家形成了单位整合、科层嵌入、精细管理与共同体治理四种依次出现又相互叠加的主导模式,呈现出深刻的内在逻辑:城市基层治理的价值基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应性,呈现出治理模式积累叠加的发展路径,在稳定性与创新性的动态平衡中,通过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发展获得持续赋能。
注:原文发表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本文摘录其主要观点。
作者介绍
张志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
一、问题提出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不仅承载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础职能,也是国家沟通社会、感知民情的重要枢纽。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脉络,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呈现出“变”与“不变”交织的鲜明特征。一方面,为适应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与不断涌现的治理挑战,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也经历了持续性的变革。从计划经济时代以单位为核心的统合型管理,到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的街居制与社区治理体系,再到当前以“智慧社区”“网格管理”等为代表的数字化、精细化与协同化探索,生动体现了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创新性与适应性。另一方面,城市基层治理又表现出强大的制度连续性。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迁,党的领导以及政府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与资源统筹能力,始终作为核心体制要素贯穿其中,为城市基层治理的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那么,应如何理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逻辑?本文聚焦于“治理模式”这一中观分析层次,运用“需求-回应”分析框架,旨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基层治理演进做出整合性解释。本文的核心议题是面对持续变迁的经济社会结构所催生的新需求,国家如何通过重塑组织载体、资源配置及技术手段等关键要素,推动治理模式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历史性延续。循此路径,本文力图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逻辑提供更为系统的解释,进而对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做出展望。
二、“需求—回应”:解释城市基层治理演进的分析框架富邦优配
“需求-回应”是解释治理演进的重要理论范式。本文运用“需求-回应”框架来阐释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需求端主要指在城市结构性变迁背景下,由价值观念、经济模式与社会结构等核心变量相互作用所激发的多层次治理需求。回应端则主要指国家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城市社会治理需求,围绕“如何有效治理城市基层社会”这一核心问题,所进行的治理要素重构。回应端包括三个基本维度:一是组织载体,即“谁来治理”的问题,包括依托单位、社区、网格等一系列不同的组织形态,决定了治理对社会的覆盖范围与嵌入深度;二是资源配置,指财政、人力、职权等治理资源如何在不同层级和主体间进行分配,直接影响着城市基层治理的效率与协同能力;三是技术手段,既包括传统的社会动员,也囊括了以信息化、智能化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在信息采集、传递和过程控制中的应用。
需求端与回应端之间并非单向的线性反馈,而是一种循环往复、螺旋递进的互动过程。一方面,每一次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都会催生新的治理需求,对现有的治理要素组合形成重塑压力。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组织创新、资源整合与技术升级进行主动回应,在解决旧有问题的同时,也因改变了社会结构和公众期望,而不可避免地催生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治理需求。因此,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在这种“需求牵引、创新回应、再造新需”的循环中得以实现。
三、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演进的历程分析
(一)单位制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确立,是对当时深刻的结构性变迁所做出的系统性回应。面对百废待兴、社会力量薄弱的现实,国家必须创设一种能将社会各阶层牢固纳入统一体制的组织工具。单位制因此被赋予了多重角色:它不仅是生产组织,更成为一个集行政管理、社会服务、思想引导于一体的“全能型”社会单元。在资源配置上,国家通过单位对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统筹与福利化分配。在管理技术上,一方面,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体系,对城市的人力、物力等关键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另一方面,单位内部通过定期的集体学习、组织生活会等形式,强化成员对集体目标的认同和组织的纪律性,将单位塑造为一个高度整合、步调一致的社会基本单元。
(二)科层化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为应对单位制解体后出现的治理真空,国家开始构建以行政科层体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模式。2000年《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以社区为功能单元、以居委会为组织载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在“市——区——街道——社区”的四级体系下,作为区政府派出机关的街道办事处负责统筹辖区内各项基层事务,居委会则承接了大量原先由单位承担的管理与服务职能。通过这种属地化管理和条块结合的方式,国家将日益分化和流动的城市居民重新纳入统一的治理网络。在技术手段上,这一模式的本质是以行政体系的纵向延伸来重构基层社会秩序。政府将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任务层层分解、逐级下达,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成为政策与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执行终端。
(三)精细化治理模式
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治理挑战,以“精细化”为核心导向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其在组织载体上的创新便是网格化管理的创立与推广。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率先试点“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模式,通过将辖区精细划分为单元网格并配备专职监督员,实现了对城市管理空间的全时段、无缝隙覆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网格化管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与组织创新并行的是技术手段的迭代。数字化转型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其一是旨在提升政府主动发现和处置问题能力的管理技术创新。其二是旨在拓宽民众诉求表达渠道的响应技术创新,“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普及为居民反映基层治理问题提供了统一入口,并推动了诉求受理、派单、办结、反馈的全流程管理体系的完善。
(四)共同体治理模式富邦优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宏观背景持续演变,对治理模式的调适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回应新时代的治理需求,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组织载体层面,党建引领成为其核心特征基层党组织更强调其统合性功能,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结构。在资源配置方面,治理重心下移仍然是主要改革方向,财政和人力等资源更加向街道和社区层级倾斜,职权范围也相应调整。在技术手段方面,表现为数字赋能与“三治”融合的协同运用。各地普遍构建了智慧社区系统、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和数字政务热线,推动诉求受理、事务流转和资源分配的在线化与实时化。总而言之,“共同体治理”模式体现为一种在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协同、共建共享与协商合作的制度体系。
四、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演进的规律特征
(一)价值基石: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应性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在根本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所驱动的。这一价值理念的连续性,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保障。在实践中,这一价值体现为“务实回应”与“战略引导”的辩证结合。治理模式的演进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同时,治理演进同样体现出国家在设定长远目标、主动引领社会发展方向上的战略角色。
(二)演进路径:治理模式的累积与叠加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并非一个新范式彻底取代旧范式的线性过程,而体现为一种治理模式的累积性发展。历史上各个阶段形成的主导治理模式及其内在逻辑、组织载体与技术手段,并未在新阶段被完全抛弃,而是有选择地被新的治理体系所吸纳、改造和整合。由此,国家手中的治理“工具箱”日趋丰富,形成了一个包含了多种治理模式及其配套机制的复合系统。
(三)动态平衡: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是在一个稳定性与创新性的内在张力结构中展开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治理的演进以高度的“稳定性”为根本前提,这源于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基础性支撑的政府行政体系这两大制度支柱。另一方面,治理的演进又充满了“创造性调适”的活力,包含了对治理问题本身的再定义以及对制度安排的再造。
(四)赋能机制: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发展
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双轮驱动”,是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演进的关键赋能机制。一方面,治理体系对新兴技术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与主动吸纳。另一方面,技术的广泛应用又反向对制度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催生政府进行内部的流程再造和数据共享,以打破“条块分割”的制度壁垒。
五、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演进的未来进路
立足于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演进的历史轨迹,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发展道路需要在把握其规律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深化回应性、整合性、参与性和赋能性的治理创新,建构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
(一)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应性,构筑民意驱动的基层治理体系
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向度在于基层治理体系回应能力的持续深化。治理体系需要超越对孤立事件的被动反应,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够系统性吸纳与整合社会诉求的制度化渠道。这就需要将“12345”等平台汇聚的海量民生数据,从记录问题的“问题库”转变为洞察城市运行规律、预判潜在风险的“数据池”,进而推动治理模式从“问题驱动”的被动调适,向“需求引领”的主动塑造转型。
(二)整合累积叠加的治理模式,建构富有弹性的复合治理框架
未来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可能并非寻求某种单一的“最优模式”,而是着力于提升对各阶段形成的多元治理模式进行整合与调度的能力,从而建构一个富有弹性的复合治理框架。其实现路径是在“党建引领”这一核心原则下,系统性地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将政府的引导、市场的效率、社会组织的活力与市民的参与统合于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之下。
(三)释放社会的创造性活力,推动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化
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稳定框架下,最大程度地释放社会内在的“创造性调适”活力。这就需要为社会参与和民主协商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空间,使之成为治理体系内在的、持续的创新源泉。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方向在于推动民主协商的常态化与规范化,致力于将协商民主从应对特定矛盾的“权宜之计”,转变为基层社会日常运行的“内生机制”
(四)推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发展,赋能普惠便民的数字治理生态
未来的发展需要在拥抱技术变革的同时富邦优配,确保“工具理性”服务并服从于“价值理性”,避免出现“技术异化”或“数字崇拜”的倾向。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应用的单向过程,更应被视为一个倒逼组织再造、流程优化和权责重塑的制度变革契机。唯有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技术进步真正导向一个更为科学、公正和可持续的治理未来。
金御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